摘要:目前市場對樓市的關注焦點更多放在了長效機制建設上,而不再是價格和成交量了。而樓市 調控長效機制建設的著眼點則有很多,如土地制度改革(集體土地入市、小產權房入市、“招拍掛”制度改革)、行業稅制改革(行業整體減稅、征收房產稅)、住房保障制度(建設資金來源預算化、保障方式再選擇、公共服務配套等)、構建市場化監管體系以及完善住房供應體系,構建階梯住房消費模式等等。比較起來,對于房價統計的關注比較少。事實上,我國房價統計存在的問題已對住房和土地資源合理配置、行業發展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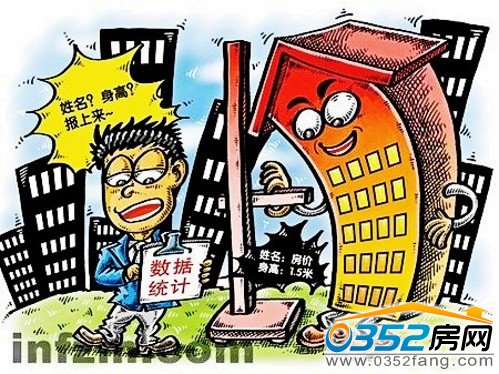
首先,房價統計指數化背離了 行業管理和市場調控的基本宗旨。自國家統計局統一發布的70個大中城市房價指數之后,始終存在只反映房價變動的共性而缺失各地實際住房價格水平的缺陷,不利于結合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來測算購房支付能力,也就不利于測算住房需求、編制住房建設規劃和住房保障規劃。另一方面,本世紀以來我國城鎮居民住房需求快速釋放,客觀上需要真實有效的房價水平來指引,而房價指數化使得各地真實房價引導居民購房置業和市場判斷的功能基本喪失,而各區域(或片區)房價的市場信息則主要通過盈利性的中介機構和數據公司來發布。這些公司或者代理房地產企業新房銷售,或者以房地產項目銷售廣告為主要經營收入來源,房價信息主五花八門、標準不一、魚目混珠,這對于引導居民購房是非常不利的,近年來居民購房的“羊群效應”不能說與此無關。
其次,房價的可比性和參考性在下降。目前,政府部門關注和披露的主要是新建商品住房的價格,而近年來調控的標的也是新房價格,比如今年3月各地為貫徹“國五條”而發布的2013年房價控制目標。但事實上,大中城市新房供應基本上布局在城市郊區,并以中心城區為原點呈現同心圓式擴張,區位特征決定了新房價格水平越來越低,新房價格變動因此也越來越缺乏可比性。二手住房由于位置固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重復交易,其價格可比性和參考性就要高得多。2011年以來,一線和二線重點城市二手住房價格上漲幅度是新房價格上漲幅度的1.5至2倍,中心城區二手住房價格漲幅是新房價格漲幅的2倍以上。二手住房價格上漲更快的原因在于公共服務配套跟不上房地產市場邊界擴展的速度,優質公共服務配套資源仍舊集中在中心城區。房價統計本應反映出這一結構性矛盾,對政府調整住房供應政策、為新房周邊公共服務配套建設提供指引,但當下大中城市二手住房價格信息散落在中介手中,無法有效整合起來為全市房價統計服務。例如,自2007年以來,深圳(樓盤)二手住房價格交易規模已超過了新房,但40%的二手住房價格信息掌握在中原等四家中介手中,60%的信息掌握在剩余的430多家中小中介手中,房價信息整合的難度很大。
再次,房價統計沒有覆蓋市場化供應的所有商品住房類型。與一般商品不同,市場化住房供應的渠道有很多,就銷售市場而言,有新建商品住房、二手商品住房、產權型 保障房(經適房、限價房、集資房等)等等。大多數一、二線城市的二手住房交易超過了新房,完全有理由納入房價統計;很多城市的產權型保障房,與商品住房的邊界非常模糊,也應納入商品住房價格統計中。此外,大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背景下,催生了城中村小產權房地下交易,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客觀上,不能不承認,這也是通過市場來解決住房問題的渠道,這部分房價交易數據沒有理由排除在全市房價統計之外。如果將所有通過市場來解決購房需求的房價數據統計起來,實際房價水平應當比公布的房價水平要低很多。例如,深圳小產權房占存量住房的一半,超過60%的人口居住在小產權房中(或租或買),如果將這些租金和房價信息納入全市房屋租金和房價統計中,深圳房價至少要比現在的水平低三分之一。可以說,由于房價統計僅限于新建商品住房,而近年來新建商品住房價格不斷上漲的趨勢誤導了城市住房調控思路。一方面,大城市在郊區積極增加新建住房供應,但由于公共配套無法及時到位,以至供應的有效性較低;另一方面,通過城市拆遷來增加新房供應,又使低售價、低租金的舊住宅區和城中村不斷萎縮,城市住房價格遂進一步上漲。
價格能否反映稀缺性以及使用成本,不僅是資源能否得到有效配置的核心,也是主管部門制定 行業發展規劃以平衡供求關系的關鍵指引。由于定價機制不合理,資源被濫用或無效配置的現象很普遍。近年來,我國城市的水、電力、土地、礦產和銀行信貸等資源,之所以出現不合理利用,根本原因就是定價機制不合理,而下一階段將開展實施的階梯電價和水價、改變“價高者得”為唯一原則的土地“招拍掛”出讓制度、開征資源稅、利率市場化等,根本上也是為了讓價格能更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性,起到有效利用資源的正向激勵。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這一基本道理,在住房市場當然也完全適用。
上一篇:小產權房得合法身份 或將觸動商品房業主抵制
下一篇:不動產登記條例開始起草 信息查詢權限正研討